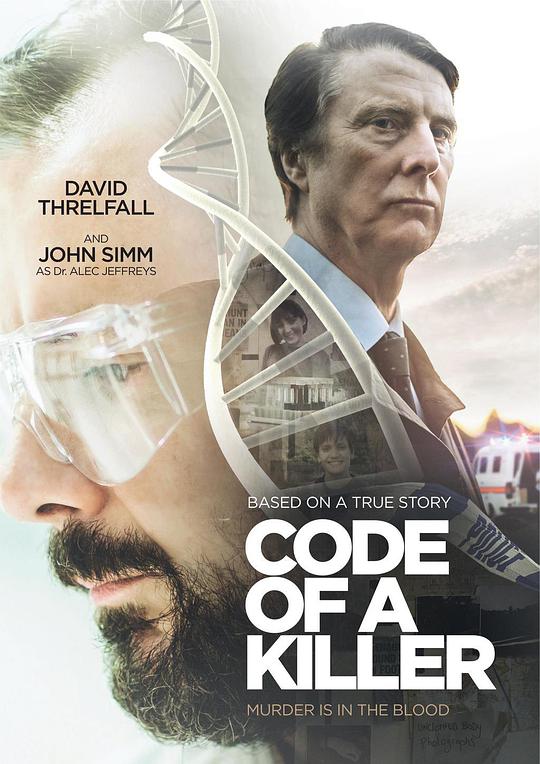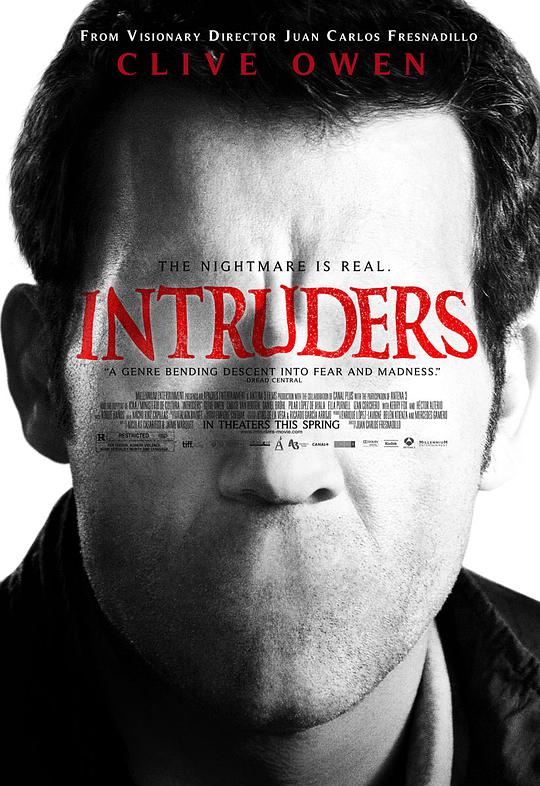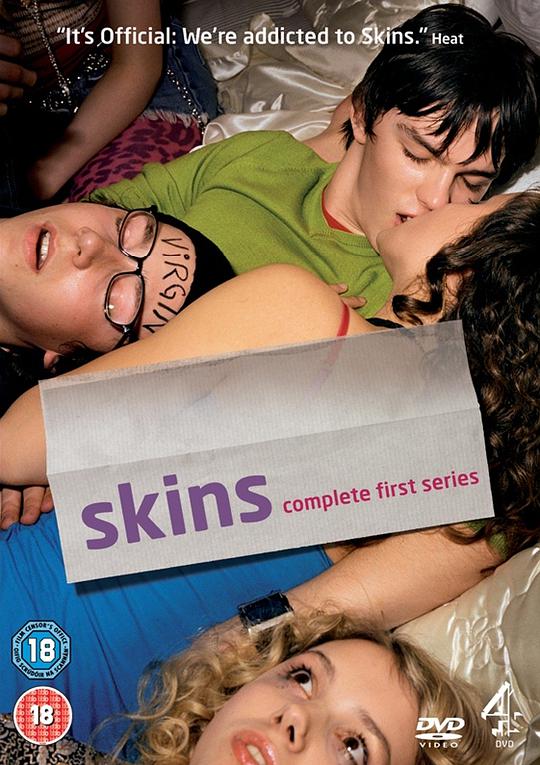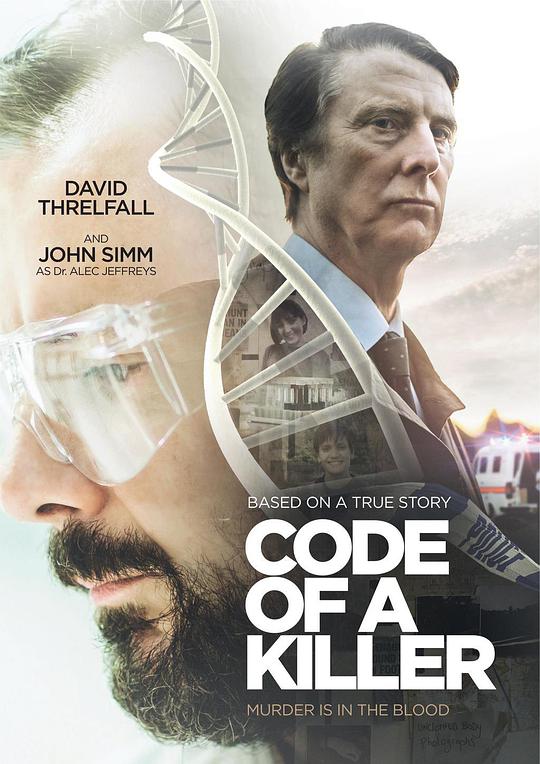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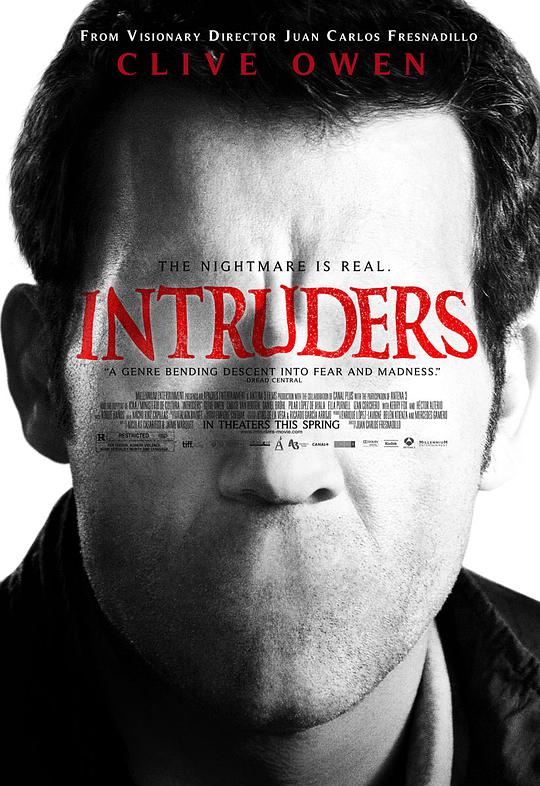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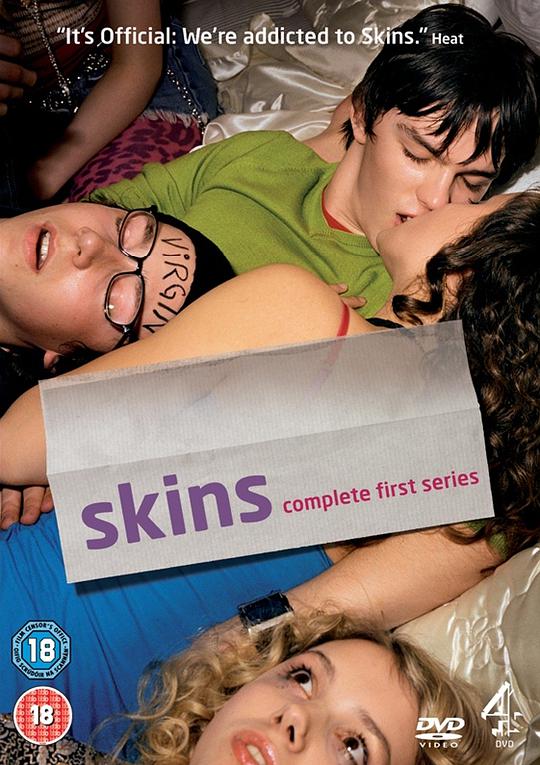








作者|谢明宏
编辑|李春晖
男人复仇得到鲜血,女人复仇得到说法。
这是硬糖君接连学习多部复仇剧后的经验总结。在古装复仇叙事中,男主经常是上来就全家被灭门,复仇主打一个“以牙还牙,以血还血”。凡是参与其家族覆灭事件的人,甭管是出人的还是出力的,哪怕是背后出谋划策的,都得上《死亡笔记》,名字逐一被红笔划除。
女主也有家庭变故,但极少全家一个不剩,而且伤害往往就来自她的家人。比如被狠心的丈夫出轨贵女后抛弃,被歪屁股的婆婆诬陷不贞洁,被娶了小妾的父亲薄待,腹中的骨肉被隐藏boss暗害……复仇归来主要是讨个说法,让仇人付出代价的同时声泪俱下地承认错误,画风秒变《今日说法》《道德观察》。
与此同时,大男主的复仇总是在“寻找爹”“成为爹”,在父权的颠覆与重建中展开。大女主的复仇则更倾向于建立女性同盟,过去是姐妹齐心,现在叫girls help girls。
总而言之,从复仇的目的到复仇的过程,男女的复仇叙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逻辑和诉求。这当然有剧集创作者因循旧的叙事模板造成的男频女频之分,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性的情感需求差异以及社会心理变迁。
“My thoughts be bloody, or be nothing worth”。《哈姆雷特》说“我的思想若不浸染鲜血的话,便毫无价值!”当越来越多的主角把复仇当成唯一目的,他们究竟想获得什么?是把敌人逐个击破的智性愉悦,还是复仇过程中的自我重建。
寻找爹,成为爹
短视频流行的“嘉豪父子对话”中,父亲总是吹捧孩子有自己年轻时的风采“我儿真乃当世雄狮”,儿子也感慨自己非池中之物“同学里根本没有与我同频共振之人”。这种看似荒诞的父子游戏,却也不无精准地洞察到男频内容的隐秘需求——寻父,弑父,成为新父。
《藏海传》中,平津侯既是杀死藏海生父的凶手,又成为他精神世界的“象征性父亲”。带他进入官场,教他为人处世,一点点将藏海培养成自己的心腹。平津侯的强大,在于他依仗其社会地位和资源禀赋对藏海进行塑造洗脑。
那么藏海对他的复仇,就不仅是为了血缘父亲的报仇,更是在推翻并取代这个精神父亲在象征秩序中的位置。事实也确实如此,复仇成功的藏海推举新帝有功,此时若不急流勇退,又将成为下一个“平津侯”。
而在这个过程中,藏海还成为了平津侯儿子庄之行的“父亲”,完成了从“弑父者”到“新父亲”的身份转换。他将纨绔的庄之行培养成风采不凡的武状元,令其崭露头角的同时也赢得了父亲平津侯的关注。在庄之行眼中,虽然藏海想要杀自己的父亲,可他也是“亦师亦友亦父”的存在。敌对当中有敬佩,爱慕之外有仇恨。
《长安二十四计》在这种“寻父”结构上和《藏海传》可谓如出一辙。仇人言凤山是看着谢淮安长大的,谢淮安想除掉仇人,就需要真正了解他的所思所想。这种为复仇而做的准备过程,正是一种精神弑父。青年对年长者的仰慕与仇恨,都有可能在无限接近对方的过程里转换成复杂暧昧的情愫,若非恋人当即父子。
在精神寻父的同时,被谢淮安掌控的废帝萧文敬,则被塑造成了他想要的样子:他的书童张默。张默对谢淮安由起初的害怕惶恐,到后来的信任服从,正是被对方的人格魅力所感召。
尤其《藏海传》和《长安二十四计》都有黄觉和周奇出演。他二人分别扮演平津侯、刘子温,庄之行、张默,刚好是两个男主的父亲/仇人、徒弟/书童。黄周配,完美解决了大男主复仇需要“杀爹”和“当爹”的双重需求。
这种叙事模式折射出男性社会化过程里的核心矛盾,一方面需要反抗既有的权威去弑“父”,另一方面又要建立新的权威去成为“父”。其内在矛盾是,通过颠覆已有秩序来确定自我,但最终又不可避免地复制了同一种秩序结构。
对于《长安二十四计》中的谢淮安来说,在杀掉仇人言凤山后,昔日的老师吴仲衡竟然成为新的反派。这对师徒既有家仇又有国恨,完全可以看作一对新的“父子副本”。
我要你承认
与男性不同,女性复仇叙事的核心往往是“讨个说法”。男性主张肉身消灭,女性则推崇精神摧毁。不但要仇人得到报应,还要让对方承认犯下的过错,在真心悔恨中蹉跎残生。
《琅琊榜》虽然常被划入男频范畴,但实乃典型的女性创作的女性思维复仇作品,毕竟最开始是在晋江连载的。
男主梅长苏复仇的终极目标,不是推翻老皇帝的统治,而是通过朝堂压力,迫使他亲口承认当年对赤焰军的错误。这一情节的精髓在于寻求对历史不公的公开承认和话语反转。对仇人的打击不是剥夺权力,而是剥夺解释权。
剧中复仇的高光片段,并不是残酷血腥的宫廷政变,而是梅长苏走出大殿时,梁帝突然下跪认错。“你要相信,朕是受了小人的蒙骗。”俺就是要讨个说法,每个女人都可能是秋菊,包括女人笔下的男人。
因此并不令人意外,同样的“辩论”也发生在仙侠剧《临江仙》中。女主李青月让男主白九思进入幻境,体验面对人间疾苦和丧子之痛时的无力感,迫使他从认知层面体验与她相同的处境,从而达到“承认”的目的。
更不用说《锦月如歌》中女主夺回“飞鸿将军”身份的努力,既是物质层面的正义恢复,更是象征层面的承认政治。要求大家承认她的能力与贡献,破除既有的性别偏见。“我今日来此就是想告诉你,无论我叫什么名字,是男是女,我都一样能成为飞鸿将军。”
正如韩剧的复仇双子星《黑暗荣耀》和《财阀家的小儿子》一样,宋慧乔苦其心志多年,就为让霸凌者承认错误,破坏她们那披着高尚外壳的伪善人生;而我们的宋仲基,重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爸爸、找爷爷,后来居然被财阀爷爷的人格魅力打动,自愿成为一员想要创造新的家族奇迹,早忘了自己曾是被财阀买凶做掉的打工牛马。
这种男女复仇的差异,显然与社会现实息息相通。长期以来,女性的经验和话语被边缘化、被漠视、被否定,因此复仇行为往往首先是一场话语权的争夺战。女性复仇者不仅要改变现状,更要改变讲述历史的方式。
而男性从小被鼓励通过行动改变外部世界,因此复仇总是咋咋呼呼急赤白脸地要改朝换代,动不动就上升到江湖朝堂等宏大叙事范畴。女性因为更多地被规训在某些人际关系领域,因此复仇总是要为自己争夺一个话筒,如《雁回时》《墨雨云间》《九重紫》其空间也更局限在家宅和院墙中。
复仇剧为何流行?
早年很少有专门复仇的剧。尽管主角开局也背负血海深仇,但复仇只是变强道路上顺手干的事,没人把它当成人生的唯一目标。
在《笑傲江湖》里活着就为复仇的林平之,是没法成为主角的。那种金庸本来写林平之当主角,后来才改成令狐冲的分析,在BBS时代相当流行。而《倚天屠龙记》更是塑造了放弃复仇的张无忌。小时候还信誓旦旦说记住每个仇人的长相,长大居然大手一挥“我原谅你了。”
搁现在,林平之恐怕会被爆改成美强惨复仇大男主,特别适合那些具有破碎感的小生。整天胡吃海喝,结交三教九流的令狐冲,哪有一点男主的样子,意志不坚纯粹丧失信念!
复仇剧在当代的流行,必然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心态。复仇剧是一种极具掌控感的叙事:主角通过一整套精密无比的计划改变命运。
当下正是乌尔里希·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。在个体化和不确定的大环境下,人们对生活的控制力减弱,而复仇提供了一种“掌控代餐”。尽管这个仇不是观众的,可每当战战和EE的计谋面临揭穿时,硬糖君都要为他们捏把汗呢。
而流行思潮越是保守,反映在文艺作品里反而有一种别样的激进,这也是近几年复仇剧如雨后春笋冒头的动因。
首先是泛滥的早衰心态。当代人生活在高度反思性的社会中,倾向于不断回顾分析自己过去的经历。在社交媒体,原生家庭创伤更是恨海情天般困扰着群众。未来不值得被期待和寄望,人们更执着于追溯造成当前困境的历史根源。
复仇剧恰好迎合了这种“为过去而活”的心理,主角将全部的生命能量都倾注于纠正历史错误,这是一种强烈的心理补偿机制。别的题材主角还能谈谈恋爱弄点人间烟火,复仇剧的主角那是吃顿好的都有罪。必须每天卧薪尝胆夙兴夜寐,拖着一副病体与仇人斗争。大仇得报那一刻,感觉血条都耗尽了。
其次是审查与舆论环境下的叙事安全策略。过去权谋一直被划红线,而复仇则将冲突给“私人化”了。这种“去权力化”的叙事为主角的行为提供了道德豁免权。因为观众天然同情受害者,使得主角的计谋和越界行为也能获得在观看体验上的情感合理性。和过去的权谋剧相比,复仇剧尽管还是有朝堂戏,但套上个体叙事后显然安全多了。
其实,看剧时比起担心复仇剧主角的安危,硬糖君更担心他们的精神状态。明明可以拥有不一样的人生,为什么要把自己封锁在过去呢?复仇剧的流行,无疑折射出某种集体情绪:
人们对过去的执念、对掌控的渴望,以及对有限表达空间中正义叙事和话语权的迂回追求。然而这一切都让人感到暮气沉沉。男性既要反抗权威、又想成为权威,女性聚焦话语权、争夺解释权,都是在破碎的世界里寻找可以抓住和重新阐释的东西。
他/她不是在规划未来,而只是想要重写过去。